所謂「異文」者,簡單而言就是篇章在流傳過程中,部分字句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差異,從而形成不同的版本。這是很常見的現象,畢竟漢語文化長達幾千年,古人在有限的條件下難以確保文本傳播完整。具體的原因林林總總,常見者可以歸納為幾種情况:第一為文字演變,一般見於先秦兩漢時期的文本。早期的文字系統較簡單,字元數量不多,惟隨着傳意需求增長,單一字形無法承受過多含義,於是出現分化,另造新字代表原有的部分含義。後世重編有關文本時,便會依當時的文字用法更新文句,以求時人明白,遂形成別於古本的版本;第二是傳抄失誤,即在複製和傳播過程中,主事者誤解文本。其中又分成「聲訛」和「形訛」兩類,前者源於早期的文章多靠口耳相傳,同音、近音、方音或口誤俱阻礙接收,而後者多出於誤判文本的文字為其他形體相似的字。許多書坊出品均來自文化水平有限的刻書工人,對文字的掌握未夠精確,多有疏失犯錯。
古籍異文的形成方式
去古既遠,資訊模糊,後人稍不經意,便會導致上述兩種情况。然而,部分情况牽涉更多人為因素,包括避諱,以及往後的回改。傳統以為君主的名字是神聖的,不宜為他人所言所書,故既存的文本都得改寫有關字眼,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時,典籍的「民」皆會改為「人」、「代」等。及至其他時代,部分人又會以還原為名,嘗試把那些字眼通通回改,卻容易誤改一些本來未有更動的字,最終造成更多異文;另外,作者在修改過程中又產生不同的版本。正如現代圖書的版次問題,古人亦會多次修改自己所作,而修改期間的稿本因應不同原因流出坊間,未得澄清又幾經年月,就會成為有別於定稿的新版本,後世頗難理清。
於文獻學而言,異文是最基本的課題,一字之差都可能延伸出重大討論。除了避諱現象之外,「古無輕唇音」的發現也是著名例子。話說清人察覺到不少異文存有規律,即古本作重唇音的字,在今本都變成輕唇音,如《尚書.唐誥》有「以殷餘民邦康叔」一句,「邦」後來寫成「封」。當然,此類課題屬於專業學術範疇,一般讀者或許不求如此深入,但異文現象的影響其實十分廣泛,文義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部分古文的異文會導致句子變得不可解讀,例如唐人韓愈的〈張中丞傳後敘〉引鄉間父老所言,謂外族賀蘭「嫉(張)巡、(許)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」,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》和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分別把「己上」改為「已」或「巳」,完全違反語詞的用法,顯然是形訛所致。又如明人張岱的《陶庵夢憶》有〈虎邱中秋夜〉一節,當中介紹作者沿路經過的景點時,「鶴澗」一地在某些版本中寫作「鵝澗」。地名是事實層面的問題,查詢地志文獻自可辨明。
上述一類異文尚算易於解決,始終許多人都會意識到錯誤所在,甚至能夠推斷正確的版本。真正教人苦惱的,是諸個版本各有道理的情况,譬如宋人蘇洵的〈六國論〉云:「蓋失強援,不能獨完,故曰『弊在賂秦』也。」香港中學生對這篇範文必然熟悉,但他們大概不知「不能獨完」還有「不能獨全」的版本。「完」和「全」的意義非常接近,不管採納哪一個版本,相信無傷大雅。問題在於部分異文的差異實在太大,直接左右理解。南朝詩人謝靈運的〈登池上樓〉可謂經典,其中「徇祿反窮海,卧痾對空林」一句在宋本《三謝詩》是作「徇祿及窮海,卧痾對空林」的。「反」是「返回」,「及」是「追去」,方向截然相反,抒發的感情也有分別。後世論者的立場分成兩派,一者認為「及」生動地描繪謝靈運逐利而往的姿態,具自嘲味道;另一派主張「反」暗示作者掙扎失敗,唯有無奈認命,詩意增添了一分悔恨。鑑於「窮海」是抽象的指稱,就算不斷鑽研謝靈運在劉宋初年的生平和心境,兩種解釋似乎都可以自圓其說。「見」南山,還是「望」南山?
至於陶潛的〈飲酒二十首.其五〉更是教材級的例子。「採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」被推舉為千古名句,但是北宋時候其實流傳了另一版本。根據《東坡題跋》,蘇軾在〈題淵明飲酒詩後〉提到:「因『採菊』而見『山』,境與意會,此句最有妙處。近歲俗本皆作『望南山』,則此篇神氣都索然矣。」從「皆作」一語推測,「悠然望南山」的版本大概不是個別情况,而是當時廣泛流通的。後世普遍認同蘇軾的意見,以為「望南山」有損詩歌意境,因為「望」傾向強調施事者的主動意味,即詩人有意把視線投向終南山,反而「見」感覺上是較中性的說法,僅陳述了詩人看見終南山的事實,與句首「悠然」一語相配。換而言之,「見」與「望」之間,前者是較為理想的選項,對淵明所賦利處不少。問題在於,較理想的選項就是符合真相的選項嗎?從異文引伸出美學爭議
有時候,異文影響的不限於文意,還會引伸出重要的美學爭議。唐人李白的〈靜夜思〉膾炙人口,任何孩子都懂得「舉頭望明月」一句。可是,看似理所當然的詩句實有別的可能性:「舉頭望山月」。作如此版本者,包括宋人郭茂倩的《樂府詩集》、明人高棅的《唐詩品彙》、清人沈德潛的《唐詩別裁》、彭定求等人的《全唐詩》等等,遍及幾代的重要學者著作(這些版本中,李白所賦的首句亦有「忽見明月光」、「床前看月光」等差異,在此暫且不論,免得分散討論焦點)。至於今人琅琅上口的版本,相信出自深受追捧的《唐詩三百首》。由於〈靜夜思〉的形式是古絕,故不能從字音的平仄判斷用字正確與否,何况「明」和「山」都是平聲,聲音效果上也不見得有高下之分。因此,討論只好改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入手。支持「山」的論者往往主張,「明」早已經見於「床前明月光」,在僅僅二十字的篇幅中重用字眼是為失誤,太白的語言能力不當拙劣如此。理由聽來充分,可是回頭一想,絕句真的有不許重複用字的限制嗎?如果這是律詩,尤其是中間兩聯的對仗句,重複用字確實不太妥當,但古絕的風格較原始,崇尚自然質樸。誠然,重複用字的絕句不算罕見,如劉禹錫的〈竹枝詞〉云:「楊柳青青江水平,聞郎江上唱歌聲。東邊日出西邊雨,道是無晴還有晴。」其用字之重複遠比〈靜夜思〉嚴重。可見絕句的作品水平取決於最終呈現出來的效果,與有否重複用字之事沒有必然關係——圍繞異文的討論,結果提升至絕句美學的大哉問。
異文現象對古典文學構成的最大啟發,當數引起論者對手抄本文化的重視。如同文首提到,人手抄寫是早期書籍的生產方法,但及至印刷術盛行的年代,手抄之事其實沒有消失。分別在於,手抄的目的不再是單純複製文本,以求流通,而是轉變為文人的雅趣與修行。藉由抄錄的工夫,他們致力體悟古人的文心,還會刻意選取、製作異文,一方面表達自身寄託,一方面與古人隔代交流。田曉菲教授著有《塵几錄: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》一書,正是深入闡釋這種現象的得獎論著。陶淵明詩文的手抄本在宋代非常流行,並如《蔡居厚詩話》的觀察,諸本「校之不勝其異,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,不可概舉」。田氏大量蒐羅、對照不同陶集手抄本的異文,包括剛才提及的「見」與「望」等,否定了區別「正確」文本的可能,以為異文均是陶淵明接受史的體現。她引用袁行霈教授的說法,提出陶集中,異文的意義有三類:修辭、正誤和生平考證。當中第一種是該書的重點,因為它涉及抄錄者的審美觀念和意識形態,亦即對陶潛形象的想像與再現。
如何應對古籍異文?
也許扯得太遠了,最後不妨回歸一個現實問題:得悉異文現象之後,一般讀者應該如何應對呢?第一步肯定是尋找可靠的版本。有別於現代作家的著作,古文作品基本上不受版權限制,任何出版社都可以沾手,以致成品良莠不齊。要準確掌握異文的情况,當求諸具備學術背景的古籍出版社。它們出版的「校本」、「校注本」都是由專門學者編纂,材料豐富,處理嚴謹,能夠就異文的取捨提供可靠說明。固然,一家之言絕不是永遠無誤的,讀者還是要勤於動腦筋。撇除傳統校讎學技巧,如對校、本校、他校等,文學知識也能派上用場。
倘若文本是近體詩的話,格律、押韻和對仗等形式要求都值得參考。至於較多變的體裁,唯有循上文下理推敲。以文首述及的〈前赤壁賦〉為例,「滄海」與「浮海」俱能成詞,單單聚焦此句難有進展。如報道言,展示東坡手筆之際,故宮南院另一展覽又有元人趙孟頫的真迹,其〈書前後赤壁賦〉用了「滄海」,可知兩個版本早已混淆。可行之法是把目光移至上一句,因為「渺滄海之一粟」實為一組對偶的下句,對應「寄蜉蝣於天地」。〈前赤壁賦〉作為賦體,以駢句為主,且時有押韻,形式縱未嚴格如格律詩,惟結構與聲音的美感始終有所講究。由此論及「浮」與「滄」的差別,即可發現新問題:「浮」與上句的「蜉」同音,位置又是相對,會否擾亂文句的聲音?「滄」是陰平聲,「浮」是陽平聲,抑揚起伏的效果是否更覺美好?詞義方面,「滄」是形容詞,而「浮」是動詞,何者適合對應上句的「蜉蝣」?邏輯上,上句以「蜉蝣」對比「天地」,那麼下句的「一粟」又該與「滄海」抑或「浮海」對比呢?諸如此類,都得納入考慮。
不過,恰如〈飲酒.其五〉的討論,美學上的勝負與文本的真實面貌是兩個關係不大的問題。蘇軾身為一代大家,後世難免假定他的作品是最出色的,但現實經驗不時提醒,天才也有失手的時刻。今人編寫古代文學史,總是惑於接納和解釋偶然的意外。况且,蘇軾自身可能對二字久無抉擇,時而「滄海」,時而「浮海」,改之又改,那麼何謂「真正」的版本?無怪乎田曉菲教授對辨清異文,還原文本的可能感到絕望。與其糾結於無解之問,不如換一角度看待異文的意義。異文無疑帶來誤解古人原意的風險,卻同時提高了讀者對文句的警覺性,促進有關語文運用方法的思考,可謂「有危自有機」。
文•凌頌榮
美術•劉若基
編輯•鄒靈璞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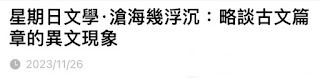



沒有留言:
發佈留言